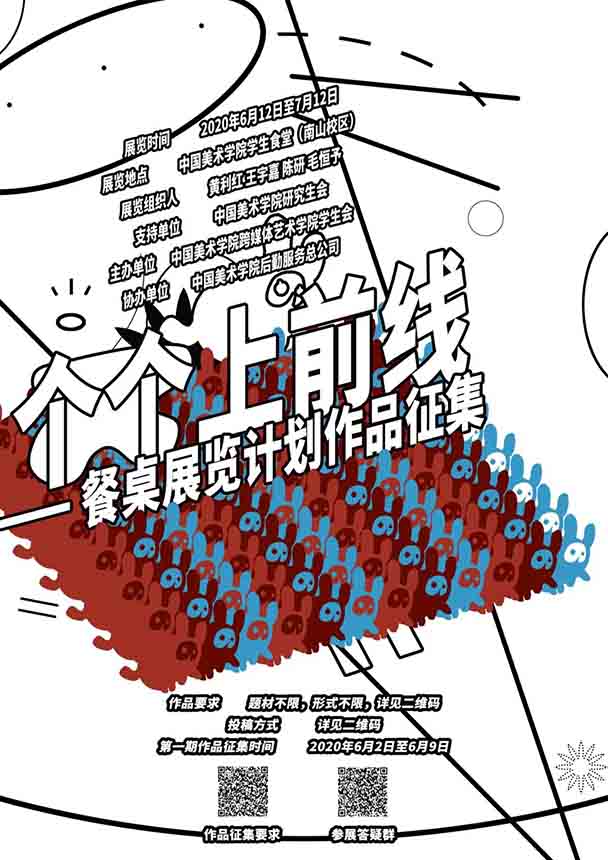29 Jun 折叠领域|跨媒体艺术学院2020届研究生毕业展
折叠领域 折叠是物的回拢聚合和翻转迭展,这种伸曲重叠受制于外力的挤压与冲击,同时也是物事转呈再启的自在系统。由折叠引发的空间思考不仅影响到二十世纪工业与建筑设计,也延展到今天的计算机理论和日常应用之中。事实上,这个话题也一直成为现代主义以来当代艺术层面不断叩问的领域。当然,不只是形式结构上的更新迭代,而更多的在于无数的思想交锋所引发的观念与媒介方式的趋进。就跨媒体艺术而言,其跨文化融合、跨领域实践正体现着某种折叠的延展与拓新,折叠领域其实也是我们立足艺术与社会的现场。 庚子新春,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肆虐全球,至今尚未得到平息。这场史无前例的浩劫改变着世界的格局,也冲击着我们庸常的生活,每个人都在经历个体与外部世界的交融和平衡,感知着身体与心灵的双重磨砺。这段特殊的体验无疑考验着我们的生命意志,也在铸炼我们的精神世界。 这场突袭的疫情与外力在一定程度上更新着我们与世界、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系,无疑也影响着2020届跨媒体艺术学院全体毕业生的生活秩序与创作安排。如果说“折叠”聚合着疫情期间来自内外种种复杂多变情势,那么这次毕业展则体现了师生一致某种化危为机的积极转呈与回应。一方面,从中感受到“折叠领域”既是他们的媒体现场,也是其社会现场,它包含着心灵空间与社会想象的碰撞,尤其是透过媒介技术所彰显的人文关怀;另一方面,也让我们看到新一代艺术家对于媒体与现实的取用立场和拿捏姿态;毕业展并非人生的界域,而意味着折叠领域的空间位移和探寻新世界的起航。 管怀宾2020年6月 折叠领域——跨媒体艺术学院2020届研究生及本科毕业展开幕式 折叠领域——跨媒体艺术学院2020届研究生及本科毕业展现场 毕业创作 再次消失作者:陈天凤导师:高世强研究方向:影像与空间叙事研究媒介形态:影像作品尺寸:不限大脑将过去的记忆和未来的梦想编织在一起创造出自我意识。但是记忆并不会完美的记录下我们的人生故事,他们会随时间改变和扭曲,一旦记忆出现问题,整个生活都将会发生逆转,此刻你是否会怀疑世界的真实性?如果失去记忆,我还是“我”吗? 消失的身体作者:DELIBASIC MILKA导师:管怀宾研究方向:空间多媒体艺术研究媒介形态:影像装置作品尺寸:不限在隔离期间,我每天我都会透过窗户,盯着外面看。但其实我什么都没有看,也什么都没看见。我只是凝视着虚空和无尽的灰暗。没有人,空间中的身体都消失了。鲍德里亚曾说过,消失永远不是完全的消失,而是一种形态变化成另一种形态的变形过程。该作品探索这空间中的虚空。装置由三个影像投影组成。两侧的影像所代表的就是身体再次连接到大地和失去的触感。第三个影像则展现了人体消失在空间之中,却又以一种难以名状的形态重新出现。 1114作者:李梦颖导师:高世强研究方向:影像与空间叙事研究媒介形态:数字电影时长:19’34作品尺寸:可变听他故事那天的日期是1114,我看着窗外鳞次栉比的楼宇,觉得这串数字像极了蹲坐在楼宇森林里的孤独小人,试图用他的渺小、困惑和失败使你动容。香港是现代高速生活的缩影,外来的他格格不入,许是迷茫和不作为留下,汲汲忙忙和穷极无聊慢慢湮没心灵的诉求——那份柔软还未触及就消散了,不经意发散到另一个时空。他们之间涌动着这样似是而非的关系,像三个被放射到不同方向的点,无法叠合成一条直线或却有一次侥幸的交汇。 睡眠,2019/10/15-2019/11/1作者:黄晶莹导师:张培力研究方向:媒体艺术创作中的个人态度与方法媒介形态:摄影、影像作品尺寸:可变睡眠在人的一生中占据了生命的1/3的时间,在入睡的时候,我们不受控制,进入梦境。梦境宛如第二种人生的体验,平行于我们的现实世界,遵循幻觉。在这件作品中,我使用大画幅拍摄我和我男朋友一个月的睡觉时间,照片的曝光时间由当天的睡眠时间决定,拍摄我和我男朋友的睡眠状态,最后呈现出来的是一组摄影,呈现我生命中的一段时光。 塌陷与逃逸作者:米一峰导师:管怀宾研究方向:空间多媒体艺术研究媒介形态:装置作品尺寸:可变事物的边界在何处?我问自己。在我们现有的认知范围内,所有事物都遵循着某种既定的规律与轨迹,然而人作为一种高智慧生物从古至今都在与这种不可抗力对峙,我们习惯尝试突破某种固化的介质,以一种近乎逃逸的方式防止陷入自我认知的漩涡。但事实上,当突破了某种屏障之后往往会塌陷进另一位面的循环之中,如此往复没有终点。我们真的需要摆脱规则吗?当回到万事万物的原点内核之后,那里是令人窒息的塌陷还是一种无我的宁静?我问自己。 大拿 人类的好朋友作者:钟昊天导师:高世强研究方向:影像与空间叙事研究媒介形态:影像装置作品尺寸:可变大家好,我是人类的好朋友,大拿。没错,我是在假设我是,在认识我的之前和之后,你都可以完全不同意。最近,我观察到一些不太平的情况,是的,中美关系。前些年,我看到两张有趣的图片,是中国乔丹和美国飞人乔丹的商标,我喜欢看乔丹打篮球,中国乔丹的图片是乔丹刚刚接到球,而美国飞人乔丹图片是乔丹正起跳扣篮,在这之前,人类发明了电影。某种不和谐发生了,好像这中间缺了一张图片,我试着画了一张乔丹屈膝准备扣篮的画,这样看上去似乎没什么问题了。但这时候,新的问题出现了,作者钟昊天对我的行为发出了质问,他在这三张图片之间,插入了三部关于我与他之间的问题的电影。他说这是《生活的影像反馈》《从图像批判中返回》《人类的好朋友的影像变身》。结果,现在情况更复杂了。你们说怎么办? 大故事作者:何佶佴导师:管怀宾研究方向:空间多媒体艺术研究媒介形态:文字装置作品尺寸:可变自2017年至2020年的三年时间里,我每夜十二点都会不间断地写一篇几十字至一千字左右不等的小故事,最终写满了一千零一夜,我将这一千零一篇小故事取名为《大故事》。在撰写整个《大故事》的过程中我精心设计了许多规律和秘密,看似毫无关联的一千零一个故事被这些规律和秘密牢牢地连接到了一起,但随着第一千零一夜的完成,这些细节在那一瞬间就已经变得不再重要。这一千零一篇故事可以是一片广阔宏大的宇宙,也可以只是一粒轻轻落在你指甲盖上的灰尘。 Mantra作者:王斌导师:管怀宾研究方向:空间多媒体艺术研究媒介形态:装置作品尺寸:可变创作灵感来源于两个有趣的事物,1 幻肢症:截肢后许多人或是动物都会在大脑中存有肢体依然存在的感觉,并且能够感受到残损肢体的疼痛。2 灯塔水母:这是一种可以返老还童,长生不老的物种。这两个意向的结合,使之联想到人类对于“永生”的叩问,我们的身体如何通过进化、升级和改造达到生物意义上的永生,而灵魂,思维与记忆如何通过转译、存储、与转载达到物理层面的永恒。 九层妖塔作者:金雅婷导师:李振鹏研究方向:新媒体艺术理论与实践媒介形态:VR作品尺寸:可变妖塔内的异兽在时光中自我重新解构与重组,出现了新的兽儿,也有一些悄然消失了,无影无踪。妖塔外紧邻的高速公路繁荣了周围的城市,高楼与高楼之间紧密地挨在一块儿。在远处,我们透过高楼的间隙看到了久违的乡村风景,忽隐忽现的。高速公路在继续铺张,妖塔被包围了起来,村庄被疏远了。 环形剧场作者:杜三川导师:高世强研究方向:影像与空间叙事研究媒介形态:装置作品尺寸:可变媒介技术、资本、用户,共同编织出了今天网络社会中的话语空间结构,人与媒介的关系被其三者之间的协同作用所改变。卢米埃尔兄弟所拍摄的那架火车,仍在技术迭代更新的历史中前行着, 它又终将会驶向何处?众声喧哗中,我梦见这样一个场景:火车拉动着无人的车厢和一个黑匣子,往复奔驰在虚构的环形剧场之中,点亮一位已故诗人的寓言。 杰作作者:李璐导师:姚大钧研究方向:数据感知与媒体艺术研究媒介形态:影像尺寸:不限狂热的、反复无常的自我哲学;激烈的、夸夸其谈的修辞性宣传手段,“真理”早已过时,成为需要被克服的障碍。清除经验现实的束缚,这是后真理时代社会所构建的“旷世杰作”。一幅美术史中举足轻重的世界名画,在数码世界的传播中成为流动的副本。真理正如像素一般随着传播而加剧折损。如果说“坏图像”是图像的幽灵,那么伪造的副本就是现实的反转与荒诞。在互联网与后真理时代的语境下,当客观事实低于个人信念,雄辩即胜于事实、立场决定是非。“真理”是在为谁辩护,谁又将获得最终的话语权。本作品以桌面纪录片的独特媒介属性,通过对现有素材的拼凑、挪用及修改,以电脑桌面的符号化视觉语言形式,展现对传统著作的篡改,以及对新闻生产、制作到传播与转译的伪造过程。公众舆论的塑造打破真理的稳定性,我们在窗口界面中“见证”遥远的历史时刻。 谁是水军/Who is the Bot作者:王茜导师:姚大钧研究方向:艺术科技与创作研究媒介形态:影像装置作品尺寸:2K, 4"我们滑动手指,转发,评论,一直在数据空间中加速向前。在人人都可发声、人和非人用户共存的线上环境中,我们在多个“我与“我”之间跳跃转换,在“我”与“我”的对抗中消解。作品将网络用户比作再数据空间中的宇航员,手指的刷动比作不停跑动的双脚,在数据空间中不停原地奔跑以获取更多讯息,不停地评论转发以获取更多的回应。构成每一个宇航员身体的文字都对应着不同的微博热点,文字本身对应着不同的评论。作者试图用这种语言凸显线上数据空间中的分裂与消解——行走与静止之间,静止与加速之间,脚下的当下与身后飘散的文字所代表的被快速遗忘的过去之间,构成代表网络用户的“我”的身体的言论与言论之间,和每一个与“我”有着相同动作的“我”与“我”之间。终极的思考:是什么诱惑着我们在数据空间的图文讯息暴雨中,勇往向前? 空气中的子集3:归宿作者:李洪祥导师:姚大钧研究方向:数据感知与媒体艺术研究媒介形态:声音影像作品尺寸:可变虚拟生成建筑重构作品《空气中的子集》迎来了其三部曲的终章。在这一章中,生成建筑的残骸分布于一个暗淡而无边际的空间中。而每一块残骸都成为了某一种声音的载体,这些残骸在运动的过程中相遇,声音也随之产生重合,从单薄变得浑厚,从简单变得复杂。而由生成建部分筑残骸重组而成的代号为“Create”的卫星缓慢循环穿梭于其他的残骸之中,带着观众聆听由每一块残骸所重新构建出来的乐章。 非完整的理想形式作者:FANNY MARIE ALIX PALDACCI导师:邱志杰研究方向:总体艺术理论与研究媒介形态:装置/影像作品尺寸:120*80*35cm,250*125*0.15cm,1080P25/一分钟我的艺术实践以环境调研为起点,以不同的表现媒材加以呈现。本系列共包含三件作品,主要研究环境中老化,腐蚀的自然过程。 第一部分为 “地表的形状”:在杭州转塘区的一块废墟里选取了一个样本,作品的创作过程像是在作一个地面的永生浮雕,又像是在做地质勘测。粉红色的塑料桌布被带到杭州城市的边缘的工地上,铺设的区域纪录了该地域形态发生的转变,这种转变结合了以前基础设施的遗骸。 第二部分为“浪过留痕”:用黑色钢板沿着海滩平铺,形成一条平行于岸边的线,潮水升起,海水留在金属钢板上,金属与带盐的海水接触而氧化,随着时间的推移,当变化发生最丰富一刻, 用清漆停止氧化的过程,试图捕捉这微小的片刻,宛若一块化石, 这是待一切都过去之后, 仍然记录着自然的化石。第三部分为“犹未定夺 ”: 绿色的水桶里释放出粉末,不断喷射入水坑,水面是表演的镜像。记录海浪的痕迹,收集土壤,沉淀化石…展示出的作品构成了一个梦幻般的景观聚集体, 我试图用不同的行 为从选定的领域中行动,来抽取其非完整的理想形式。 迹忆作者:李朝林导师:姚大钧研究方向:数据感知与媒体艺术研究媒介形态:VR作品尺寸:可变在转塘,我们目睹了“城中村”这个孤立而滞后于时代发展步伐的空间被主体城市覆盖、吞噬,并逐渐消逝;它只是中国众多“城中村”的一个⼩小的角落。从一开始的⽣生机勃勃,到最后成为一⽚被推倒的废墟;在其被一步步吞噬的边缘地带游离中逐渐显现的矛盾和冲突无可避免且日益加强;应当如何理解城市化进程与生态环境的关系. 炽热作者:郑丽镇导师:管怀宾研究方向:空间多媒体艺术研究媒介形态:动物毛皮、麻绳、喇叭、数控集成板、灯、铁作品尺寸:可变七本动物毛皮缝制的书籍散落在空间中,高低错落有致,麻线串联而成,贯穿整个空间,像一幅风景。这是我尝试去构建一场彻底颠覆传统的经验和既定程序的臆想游戏。看着那人造书籍里血染鲜活般的伤痕,触碰时却是宣扬功勋、财富及成就的欲望。看着那人造书籍里残存的温度逐渐消逝,映衬出却是对物质糜烂的炽热追求。只要炽热的欲望还猖狂,这一切依旧荒唐。在我看来,在对自然历史与文明进程的短暂叙述中,材料语言背后所影射出的庞大能量无疑会在内心深处会留下一道道灼热的伤痕,也往往会牵连起某种难以名状的悲情。 浮光·光影艺术季+异空间/BIZARRE SPACE作者:陈应玮导师:李振鹏研究方向:新媒体艺术理论与实践媒介形态:影像作品尺寸:可变作品一,从主题词“浮光”和“光影艺术”的属性出发进行充分思考,并试图准确的体现光影韵律进行光影书写,同时动态海报是这一主题视觉最佳的呈现。作品二,异空间/BIZARRE SPACE是生活中的动物静物或是场景定格,真实的物体和错杂的空间组合,以蒙太奇的手法进行拼贴组合,置于数字窗口中叠化空间。 Access_Granted--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作者:马正阳导师:姚大钧研究方向:艺术科技与创作研究媒体形式:数字装置作品尺寸:可变暴力与物理所带来的物理改变也并没有单单停留在数字的层面。19世纪的英国由于机器工业的发展,传统的工人逐渐面临着失业。那些刻在钢板上的金属空洞并没有刻在纺织工人的身上,可却遭到了纺织工人的肆意报复。卢德运动(luddite movement)既此开始。机械被砸烂,工厂被销毁。工人们想要介此,争夺机器抢走的,原本属于他们的工作与权利。可暴力并不止于此,英国政府对卢德镇压也即刻开始,以暴治暴的故事从不会结束,持续而不可避免地永恒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