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 Aug 复岛计划与历史中的声音——高雄点唱机里的社会图景
复岛计划与历史中的声音——高雄点唱机里的社会图景
黄孙权
一
田野的目的不是为了做作品,而是尝试回答地方与空间提出的问题。
复岛团队于2011年左右组成,因应基地条件的不同,组织不同的艺术家参与。因为“不便之真相一环境艺术展”展览的邀请,我带领高师跨艺所的研究生开始进入旗津的长期田调工作。旗津是西方进入台湾的起点,也是台湾首次接触现代西方医学、基督教与棒球运动的地方。我与学生们先从王聪威小说《复岛》与《滨线女儿一哈玛星思恋起》的阅读讨论开始,思索真实地方资料、历史与想象的异同。特别是《复岛》一书,透过魔幻写实构造,王聪威将地方视为所有人共同生活的空间,是历史之地,当下之地,想象之地,地方是多时间与多空间的叠合之处,是事实与传说,亡灵与居民共存的地方,给予研究团队很大的启发。历经约莫半年的口述历史采集与政治经济学的探究,作品《复岛》制作了互动触控荧幕,以漫画式的说故事方法展示旗津人、事、物的装置,以AR[Augmented Reality]技术制作开放软体程式提供免费下载,参观民众可利用手机下载软体后,透过现场制作的图示来“亲访”旗津重要地点。旗津战和馆展览后,由于居民反应热烈,高雄市观光局要求能够搬至新贝壳馆延展一个月,《复岛》成了整个展览中唯一被要求延展的作品。
2013年我们又在高雄的捣蛋艺术基地与旗津战争和平纪念馆展出《2013复岛》,小组将原本的互动装置延展成绘本,并制作了旅游卡在往返旗津的渡轮上发送,人们在去旗津之前就可透过手机遍览旗津重要的景点历史。展场展示计划变成行动展示计划,主动邀请观众,拜访不会出现在旅游书上的景点。我与团队仍继续研发技术,希望日后民众可透过手机对着景点建物或风景,以手机的定位系统连结到程式,自动跳出景点的历史照片与说明,连结上居民对景点的记忆故事,完成自动导览的叙事机器[autonarration machine],让居民成为地方内容与作品内容的作者。

对我来说,《复岛》是一个不断进行中的计划,突破“田调/展览”的局限。地点总是叠合了地域与时间的故事,如何创造地方[site]认知与叙事的可能形式,攸关生产复数公共历史[public histories]的机会。由是,复岛从作品名称成为工作小组的名字。
在今年初,我与复岛团队进一步尝试以照片说历史。作品《录地景memo-scape》透过社区老照片工作坊搜集有意义的老照片,以旗津与盐埋两个高雄最早发展的地区为主。团队寻找老照片中的人物与景色,说服人们回到原地点重新拍摄,寻人寻景的行动,不但让我们进入田野时有带有独特的观点,且可连结都市过程中被拆毁、掩没、消逝的人际关系与地景,透过老照片的“复刻”,连结人群情感与空间记忆,亦即,桥接历史[[bridging history]。此作品于今年4月于台北的立方计划空间展出,6月21日则回到社区一栋位于哨船头由民居所改建成的小型艺术空间“白房子”展出。
自动导览叙事机器,人物地景的桥接计划,都是我与复岛团队思考之艺术生产路径:人群与历史的田野就是创作过程,作品则是我们与地方居民,历史与当代记忆交织的暂时性成果。
二 以声音诉说高雄的历史
这些尝试后,高美馆的“造音翻土”展览,我给了自已一个难题,如何要用声音来说历史?声音是时间的艺术,然而声音艺术似乎总是着迷内置时间的分配技术,呈现出某种反社会时间的倾向。似乎将生产出特定声响的时空背景清空,声音就有机会成为主体,而非其他情境的配角,直接引发身体反应。因之,不熟悉化反而是声音艺术流行的操作。
在近年高雄田野调查工作中,我对地方的历史感很多时候是由声音所激发的,特别是令我感受到冲突矛盾的,历史叠合之声。检视令我困惑的声音之转变冲突,以及冲突感如何能够创造阅读历史的新感受,声音作品如何思考社会时间(历史)的转折,是《高雄点唱机》(图1)开始的初衷。我拟定了几个重要的地点,与团队共同讨论地点的历史与其声音的历史,透过实地声音采集,历史声音的转录,团队的混音剪辑与音乐编制,选择点唱机做载体,让民众自选要面对的历史。
这十二件主要作品,代表了我们对于高雄城市历史的关切,是高雄城市发展的主要声线,也是召回抵抗声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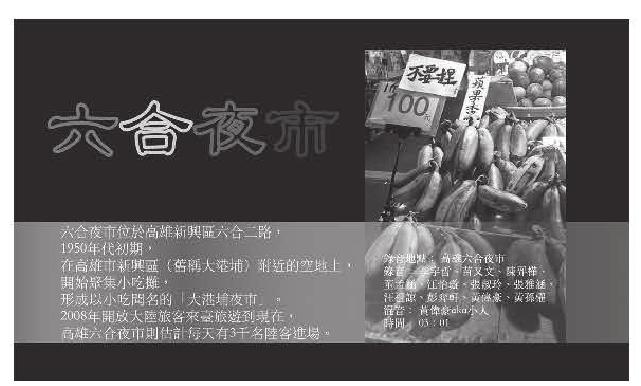

三 移民、劳动与街廓的变貌
高雄面临新的与残酷的历史。例如,陆客彻底改变了“六合夜市”(图2)叫卖声音与腔调,与街口书店广播中国禁书与政治秘辛的广告形成新的声景。七贤路上的美军酒吧被新的东南亚移工杂货店与KTV取代,香蕉码头不出口香蕉迎来陆客,《港都异国风》不再是冷战结构中的美国之音,而是亚洲内部的劳力输入与观光输入。大林蒲因为南星计划(自由贸易港区)与游艇码头的开发,一个傍海维生的村庄孩子连《海边在哪里》都不确定,当地凤林国小的校歌中“高雄港、大林蒲、椰林浪花好风光”早已不再。世运主场馆的兴建对后劲居民来说只是短暂的嘉年华,让人忘记了后劲反五轻是台湾环境运动的里程碑,围场抗争三个月以及首次的公投,大多居民都有类似的共同记忆:地下水可以点火燃烧,抽烟偶会发生爆炸。在往后三年间,抗争仍持续不断,最后虽留下新台币15亿元回馈基金以及廿五年后迁厂做为交换条件,居民《我爱后劲不要五轻》(图3)未曾停歇。香港导演梁哲夫的“高雄发的尾班车”、“台北发的早班车”,描写的都是 1960年代台湾首波都市过程和城乡移民过程,纯朴青年北上离乡背井奋斗赚钱,这几乎是全台湾普遍的感受,台语歌的恒久主题。五十
年后的今日,高雄无法阻止人口外流,然继续以卖地炒房支撑市府财政,北上工作者仍然搭着尾班车,而高铁变成北部人炒房快速通道。这个往北工作往南炒房的<移居列车>是旧劳力新资本的运输。
高雄有令人健忘的历史。例如,《美丽岛》游客络绎不绝,游客们惊叹花了上亿的玻璃光之弯顶,却鲜有人知道为何叫做美丽岛站,这不正是高雄市府将橘线红线交会处刻意放在此处取名美丽岛站之失败?这里曾是高雄最骄傲的民主运动发源地,诉求“没有名的政党”《美丽岛》杂志社的高雄服务处,1979年爆发民主运动史上重大转折的“美丽岛事件”之所在,现在只剩一个与历史毫无关系的艺术品与捷运重复的声响。
四 隐匿的历史与过去的荣华
高雄有着隐匿的历史。例如,旗津的实践新村。1955年一江山战役后,政府撤离浙江沿海大陈列岛上的居民。在全台规划了三十多个大陈义胞新村做为安置,包括了高雄旗津的实践新村,一个《离岛之岛》。五十多年过去了,大陈居民的第二代大多选择离开当初来台时赖以栖身的新村。现在,实践新村里错落着台州话的闲聊及麻将局的嘈杂,老一辈的大陈居民、当初感念领导人恩惠而建的蒋公庙和斑驳的屋舍,如岛屿般待在这个被时间遗忘的角落。仍穿着大陈传统服饰的婆婆用不流畅的国语说:“当初来台湾的时候,好苦好苦。”犹如旗津灯塔的传说,如果你深夜聆听,会听到全岛的呢喃,《听好了,我说的话别告诉任何人,这是秘密》透过旗津各地的录音,将呢喃变成声响。
高雄有着荣华历史的尾声。高雄在民国60年左右因为娱乐与社交需求,出现大规模的歌舞厅秀场表演,于民国70年至80年间达到高峰,大饭店甚至可负担廿几位乐手的大乐团。“雅士大乐队”(图4)领班苏老师,是1960年代当红蓝宝石大歌厅聘请的乐师,至今仍是高雄音乐圈当中数一数二的资深前辈,每日的表演皆无排演,借由乐师绝活,视谱便可合奏,透过苏老师的发号司令,不管是老歌、新歌、快歌、慢歌都可轻松的随时组曲衔接,歌曲排序调节舞客该怎么跳的形式。这是高雄最后一支大舞厅乐队。
历史之外,仍有新声。《废核家园》为2013年3月反核运动所作,由客家歌手领衔与高师大跨艺所学生一起录音演出,并在反核游行当天拉着喇叭游行。而甫获金曲奖最佳新人提名的嘻哈歌手小人,则展现新一代高雄人音乐创作能力,《怪物》为世界不寻常之人的幽默反击,《凶手不只一个》则是说出新世代压抑的普遍感受。
视觉总是被景观中介着,这时候,声音或可重新发现未被景观中介的历史,那些曾让我们熟习所居,却最容易遗忘,需要再次召唤的声音。因为聆听可以成为抵抗遗忘与前进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