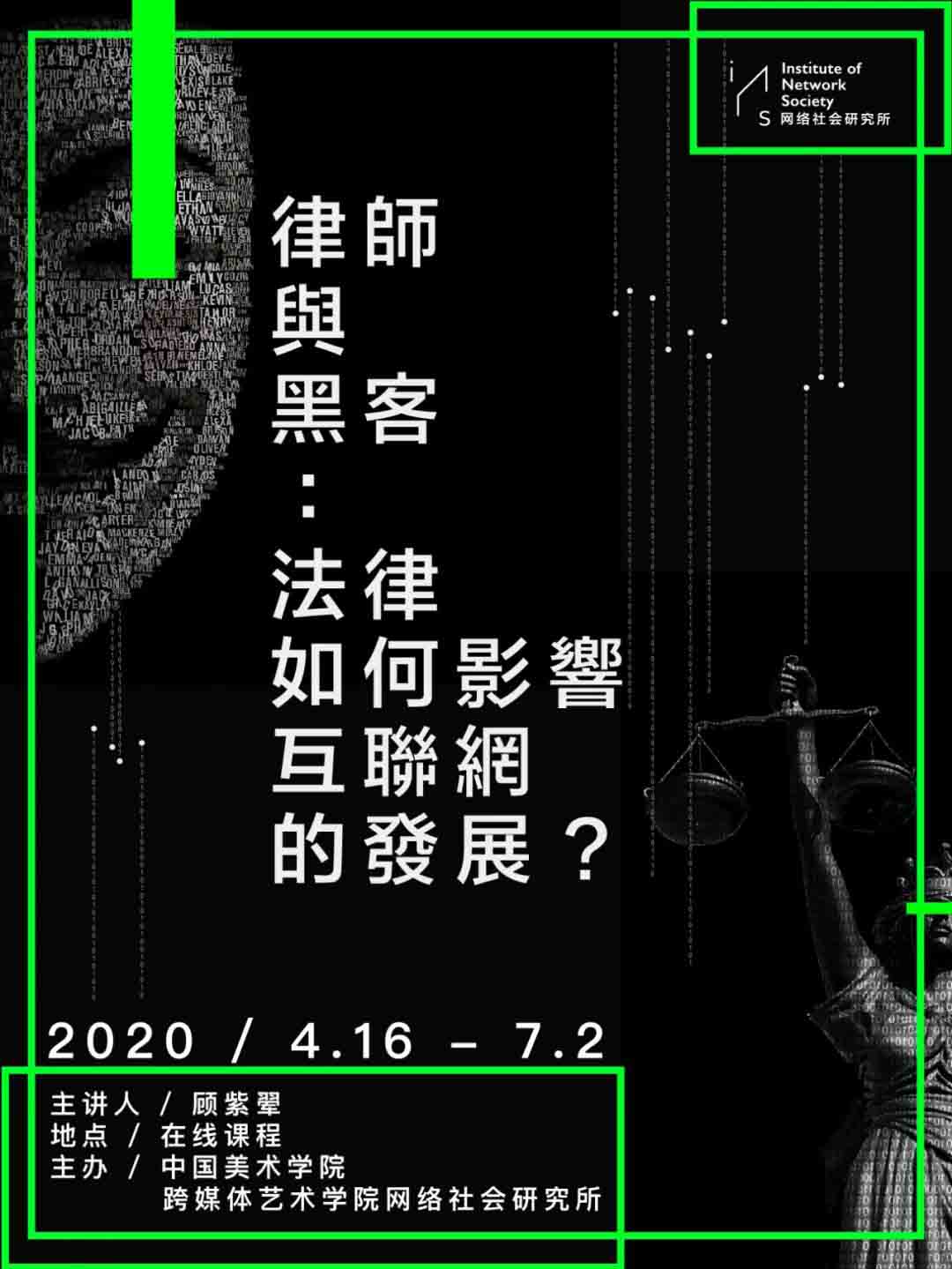04 May 创作集体或悖论体?
创作集体或悖论体? Creative Collective or the People of Paradox? 陈界仁(Chen Chieh-jen) 各位尊敬的老师与同学们,大家好。 虽然我常与劳工、失业者、社会边缘群体、社会运动者等合作,但我深知,无论是我自己或外在的客观条件,都还存在诸多局限,所以我只称这种合作方式为某种“临时性社群”。 同时,作为一个从未在学校内真正教过学的艺术家,在收到晓林寄来的“以创作集体为方法——2019·感受力论坛”的邀请函时,尤其在拜读完邀请函的文字后,一时深感困惑,尤其对此次讨论的主题“以创作集体为方法”,实在有点不明其真意,分不清要讨论的是“集体创作”,还是“欲创作/创造新形式的‘集体’”。前者容易理解,后者则几乎是天问式的大哉问。 询问晓林后,才了解要讨论的是“创作‘集体’”,对此,我必须坦率地承认,我是无能给出任何具体的建议,同时这也让我产生更多的困惑。在提出这些困惑前,请容我再次强调——因我从未参与学校的教学,自然不可能知道每位老师的教学理念与实际的实践方法,所以以下的问题,纯为我对自己的“自问”,希望在这些“自问”中,能有少部分会触发后续的讨论,至于应有不少的“多余之问”,就请诸位老师与同学们直接搁置,不用理会。 我的“自问”如下: 无论——集体、共同体、共同意识所形成的规范、与共同意识同时生成的排除构造、排除构造下被排除的“异己”,以及允许“异己”存在的共同体与不允许“异己”存在的共同体的差别、强共同体对弱共同体的吞噬、强共同体与另一个强共同体之间的倾轧与斗争、被排除的“异己”的联合与对共同体的反扑……以上,大约是人类社会从农牧时代、工业社会到网络社会的基本社会运动形式,差别只在于随着技术的发明与发展,而使运动的操作技术与外显形式有所不同,但其内核恐怕是如此循环,反复发生,且暂无止息。 我的意思是:从以血缘为联结的宗族、部落,再发展到城邦与国族……人类社会为了生存,从来就是以集体的形式存在,也一直以各种理由形成、创造新的共同体。即使是所谓“孤绝的个体”,大多是指个体在精神上的“孤绝状态”,而非物理上的孤绝。这种精神上的“孤绝”,也大多关于(但不限于)两个基本原因。一种是因个体不具有高生产力或在生产工具改变后,无法适应新生产工具与生产模式,成为被淘汰的“无用之人”的孤绝者。另一种是不完全认同当前社会的生产方式、分配方式、社会运作模式,以及共同体的共识逻辑,而成为持有异议的异议者,并因此被共同体排除的孤绝异议者。 同样的问题,回到当前全球艺术机制的范畴内讨论亦然。 直白地说,所有非西方区域的当代艺术生产,其欲望几乎皆以趋近西方无论左、右派的逻辑为“中心”,至今未曾真正改变(即使是所谓的“地方性叙事”,若仔细检阅,可发现其中或多或少都隐含、内存一个以西方“中心”主义的视域在审视自身的吊诡现象)。 换句话说,此刻,当我们说“跨媒体”时,这里所指的“跨”,究竟是只指“跨媒体”,还是包含“跨向新社会形式的实验”?如果是后者,那么: ·我们所欲实验的“新社会形式”的想象为何? ·有多少种目前可实验与实践的“新社会形式”? ·其中包不包含与“异议者的联合”? ·如果包含,那么不同异议者之间,如何“合”?或如何在“非合”的状态下形成“另类集体”? 以上问题,当然也是大哉问,同时也必然会因人、因事、因时、因地的不同,而不可能有一套统一的运作方式。但如果我们找不到相对好的方法,那如何“创作集体”,而不会滑向以高效为标准的分工逻辑?——也就是回到传统的“集体创作”的套路中。 在我的认识与想象中,要能开展“非合之合”的“另类集体”实验,至少要先面对集体的核心危机是什么。对于这个问题,我想还是再回到当前全球艺术机制的范畴内讨论,免得因问题过大而失焦。简言之,如果各地艺术领域中的异议者,不面对我们欲望构造中深埋的西方“中心”主义,那么无论怎么“跨”,都只能在被“中心”划定的范围内,做所谓的“跨媒体”艺术,但如此之“跨”,等于未“跨”——为了扼要说明我的想法,还请谅解我上述过于简化、直白,更不够准确的表述。 我的意思当然不是反西方,更不是主张民族主义、亚洲主义、第三世界论式的联合,在全球化、后网络时代后,这类联合不但已被证明无效,更容易陷入无愿景式的防卫性姿态。至于“中心”是如何形成的,以及“中心”内部的“边缘”或“边缘”内部的“中心”,以及“多中心”“去中心”是否是其他可能性等诸多问题,就留给大家讨论,不在此展开。 我的意思是:只有全面开展多种“另类全球化”的想象与实验(虽然这是一个毫不新鲜的词汇),唯有如此,西方才不再只是西方,各国也不再只是各国,寰宇四方才可能皆为“非域之域”——一个能让各种异议自由进出与共存之所。如此,感受力才可能因各种异议的存在,而被真正地打开,山水才可能成为“集体”皆可游的山水,VR才可能成为包含“多重视域”的“集体”全视域,剧场才可能不只是剧场,而是多种社会生活与社会空间的“集体”实验场。 当前全球的现实政经结构,固然会阻隔这一切的开展,但我们“生产艺术”的意义,不就是为了“跨”越这一切阻隔?而“跨媒体”不正是为了跨越真正的阻隔,才必须去实验那些媒体,可帮助我们去跨越现实中的某个具体障碍? 看见阻隔,才能看见那些媒体的集合,是可作为消解阻隔的工具。 看见阻隔,才能让各种异议者,可以形成“非合之合”的“集体”——无论这个“集体”是短暂的聚集,或是会持续深化合作的“集体”,但只有先看见阻隔,“非合之合”的“集体”才可能发生。 我的“自问”,大致如上,未能与诸位共同进行更细致的讨论,还望见谅! 祝会议顺利推进。 本文原刊登于《画刊》杂志2020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