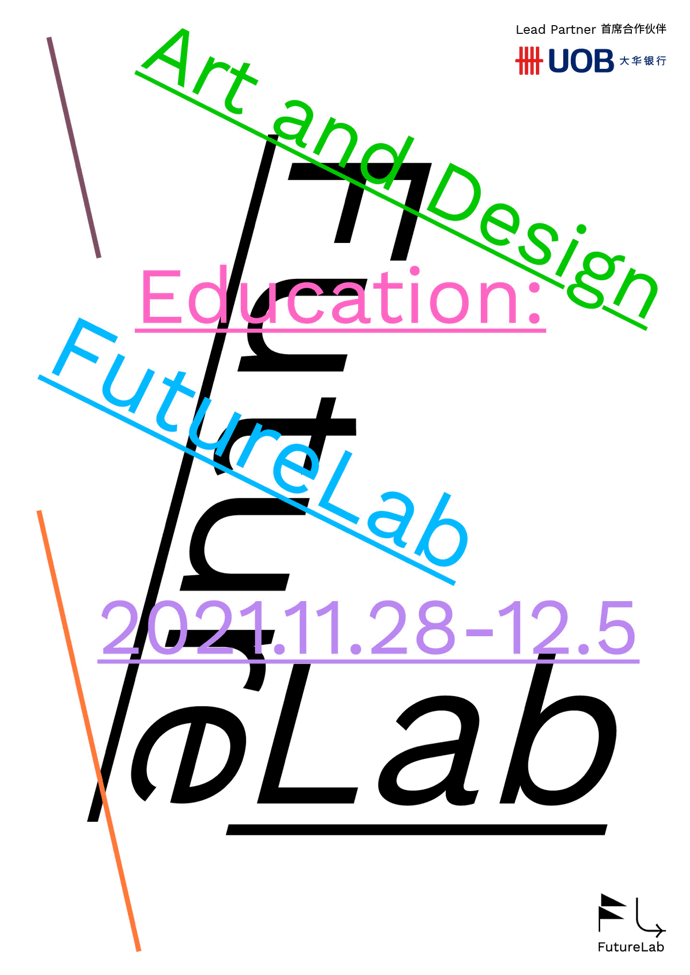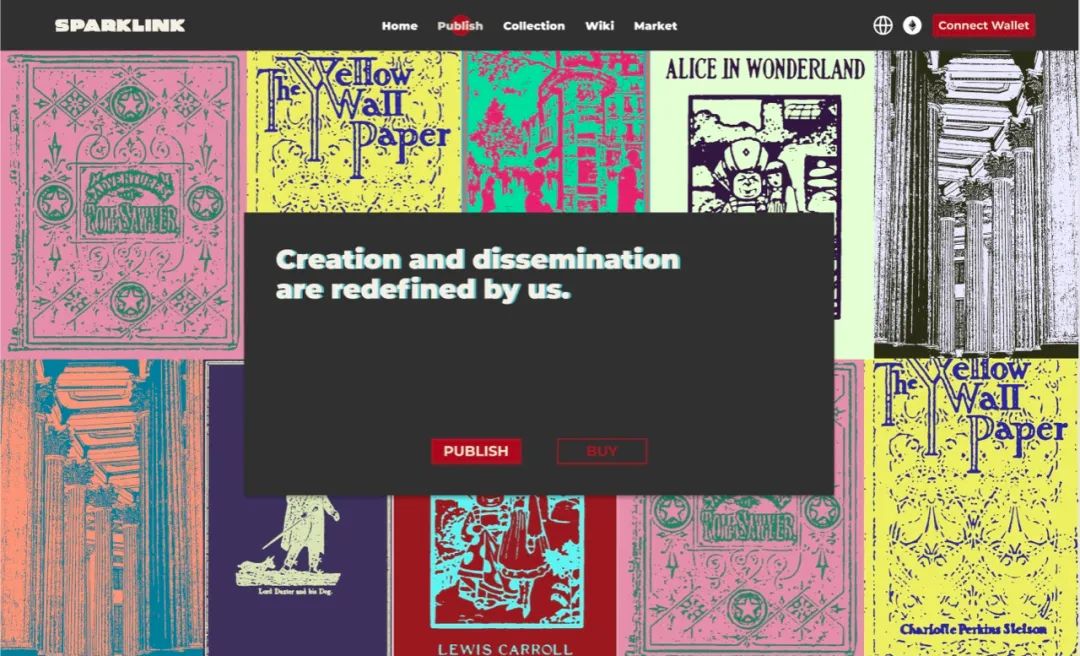展览|科艺先锋——2021家庭编年史课程艺术创作实践展览
开幕时间 2021年12月30日上午10:30展览地点 中国美术学院南山校区3号楼2楼展厅 策展人 牟森 参展艺术家 2019级媒介展演系本科生 主办单位中国美术学院跨媒体艺术学院党委 中国美术学院跨媒体艺术学院 承办单位 中国美术学院跨媒体艺术学院媒介展演系 —— 项目介绍 科艺先锋——2021家庭编年史课程艺术创作实践展由跨媒体艺术学院媒介展演系创作和制作。展览聚焦叙事工程——家庭编年史课程,将专业课程与党建和思政建设课程结合在一起。叙事工程是媒介展演系的核心课程,有空间和时间两个面向。家庭编年史为时间面向课程系统,以“场/瞬间”为基本教学元素,由场次安排、场景设定和场面调度三方面的课段构成。同学们围绕着“家庭、家族、家乡”进行探索,并梳理出了不同地域状态下,不同环境视角下的家乡志。十九位同学、十九个档案、跨越三代人,以自我家庭为视角的思考,截取家庭群体个案,深挖“中国家庭”故事,通过家族相册薄、家庭大事记、家庭编年史剧集大纲、家庭场景微缩模型、家乡图景渲染图及家乡城市地图等多种方式,呈现出充满生活感情和奋斗生气的历史记忆。 前言 关于生命的本质时刻的探索 文/闵罕 叙事演练 叙事工程是中国美术学院跨媒体艺术学院媒介展演系的核心课程,有空间和时间两个面向。家庭编年史为时间面向课程系统,以“场/瞬间”为基本教学元素,由场次安排、场景设定和场面调度三方面的课段构成。由跨媒体艺术学院学生党支部和跨媒体艺术学院媒介展演系师生联合组成的实践团队聚焦“家庭编年史”课程进行艺术创作和表现。 青年创作者们围绕“家庭、家族、家乡”,梳理出不同地域状态与环境视角下的家乡志。透过叙事的方式,演示每一个特殊个体在家族群体中的社会关系。思考个体在族群以及社会历史图景当中所处的位置。在叙事的“重复而带出的差异”当中,在再现的过程当中,采用叙事演练的方式,用独特的发声位置演示了具有独特性的时间中的生命世界和社群历史,打通了历史话语的叙事维度与意识形态维度勾连互渗的渠道。“自我”以叙事的活动,以再组织的日常空间,对自己的过去作回顾、作透视。 模型空间 在每一个模型叙述空间当中,亲身与个人的经历,都与社会、政治和生活息息相关。主体的经历在时间与社会的不停变化中,形成了身份和认同。主体也得以在从个人到家庭的连续空间中形构文化认同,以适当的回应社会的变迁。从个人的经验、个体所经历的空间和历史,来做主动的介入和交锋,模型所展现的私密空间与外在社会空间形成一种建构的关系来展现社会政治。相较于与历史、进步、文明、科学、政治与理性相关的时间,空间则时常与静态、复制、怀旧、感情、美学、身体形成另一种隐喻关系。大卫·哈维说:“社会关系总是空间的,并存在于特定生产出的空间框架之内……从这一点出发,接下来是空间关系生产……是社会关系生产,即改变一个就是改变另一个。”媒介展演系的《家庭编年史》作为集体时间性的空间组织,展现了过去和未来一并在场的时间与历史现实。 生命的本质时刻 在迅速的社会变迁中,青年的想法观念、价值态度与有时无法和成年人形成一体的整合。然而家庭编年史这个课程,让青年创作者基于个人家庭为出发原点作历史梳理,重新观察与反思自己所在的历史位置与生命时刻。作品中展开的家庭、家族、家乡之间,人与人的关系,让我们看到那些重要时刻、生命的本质时刻、存在通过其获得意义的时刻是怎么样的。看到爱与乐,苦与痛,希望与荣耀这些生命的本质时刻。希腊人用bios来精确的指示这些生活艺术所包含的东西。它意味着:具有生命的特性,生命存在的特质。然后有bioun这个词,它意味着:经历生命(vie)。Bios是某个既可以好又可以坏的东西,而我们生活的生命是因为我们是有生命的存在,生命就是自然界赐予我们的。这个能够被定性的生命,带有生命中事件的生命,带有其必然性,但也可以是我们自己规划的生命,自己决定的生命。十九位创作者,十九个档案,家庭编年史的每一件作品都感动人心,承载了青年创作者的生命经验和情感力量。 Remembrance...